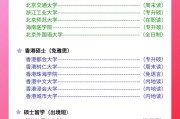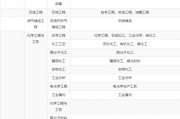她监考我,笔尖划破的不只是试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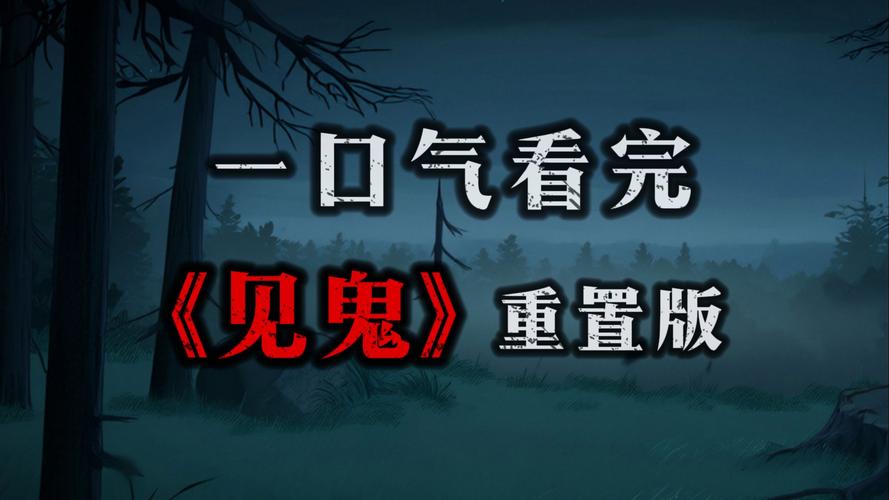
考试铃响,我抬头瞬间血液冻结:
讲台上冷若冰霜的监考老师正是三年前不告而别的前女友;
她目光扫过我时未起一丝波澜,仿佛我只是陌生考生;
直到交卷前五分钟,她悄无声息递来一张纸条:
「最后一道题答错会死——不是比喻」;
我瞥见她的裙摆下,露出一截非人的机械肢体。
考试铃像一柄冰冷的铁锤,砸碎了礼堂内最后一点窃窃私语。空气骤然绷紧,弥漫着旧木头、灰尘和一种近乎凝滞的紧张。我坐在靠过道的位子,指间的笔杆被汗浸得有些滑腻,深吸一口气,试图将那些盘旋在脑海里的公式再加固一遍。
抬起头,预备迎接监考老师例行公事的目光。
然后,时间死了。
讲台上,那个女人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职业装,衬得肤色愈发冷白。她指尖夹着一份名册,微垂着眼,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清晰、平稳,没有一丝多余的起伏,每一个音节都砸在冰面上。可我的世界在那一眼里已无声地崩裂,碎渣扎进心脏,每一次搏动都带来剧痛的窒息。
林薇。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足够一座城市褪旧换新,足够一个人面目全非。她当初消失得就像被大地吞没,没有告别,没有理由,所有联系方式瞬间失效,留给我的只有一个巨大、空洞、回响着无数诘问的黑洞。
而此刻,她站在这里,站在弥散着劣质粉笔灰和无数人命运焦灼气息的考场里,成了一个符号般的监考——林老师。
她的目光扫视全场,平稳地滑过我的脸。没有停顿,没有惊诧,甚至连最细微的涟漪都没有。那双我曾沉溺其中、以为读懂过所有星辰与夜色的眼睛,此刻是两口深冬的枯井,只有反射性的、职业化的冷漠。仿佛我只是日光灯下又一个模糊而焦虑的考生甲,与她过往人生中的任何一片碎片都毫无瓜葛。
一股冰寒顺着脊椎急速爬升。
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撞着,声音大得我几乎疑心整个考场都能听见。我猛地低下头,视线死死钉在惨白的试卷上,铅字扭曲蠕动,无法拼凑出任何意义。呼吸变得困难。是她吗?真的……是她?无数个问题像沸腾的气泡在脑中炸开:为什么?怎么会?她去了哪?现在又算什么?
一场荒诞到极致的噩梦?
指甲掐进掌心,锐利的痛感刺破迷雾,提醒我眼前一切并非虚幻。我强迫自己再次抬头,近乎自虐地去确认。
她正侧身看着窗外,侧脸线条依旧清晰得令人心口发紧,只是那份熟悉里淬上了一层完全陌生的、坚硬的光泽。她巡视考场步伐稳定,高跟鞋敲击水磨石地面,发出规律的回响,一下,又一下,像某种倒计时。
我试图答题,笔尖却在纸上划出凌乱无意义的痕迹。大脑拒绝工作。全部的感官都不受控制地聚焦在她身上——她走过我身边时带起的微弱气流,她身上极淡的、一种冷调且不像任何香水的气息,她拿起一名考生的准考证核验时低垂的眼睫……
每一次靠近都让我僵硬如磐石。
考试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周围的沙沙书写声、偶尔的咳嗽、翻动试卷的哗啦声,都模糊成一片遥远的背景噪音。我的世界只剩下那个在过道间移动的黑色身影,和她带来的、几乎将我碾碎的寂静海啸。
交卷前五分钟的提示铃响起。尖锐刺耳。
完了。我望着大片空白的试卷,心头一片冰凉的死寂。
就在这时。
一片阴影极轻地笼在我的桌角。她没有看我,目光平视前方考场,仿佛只是无意经过。可一只苍白修长的手——那曾与我十指紧扣、温度灼热的手——以一种快得几乎产生残影的速度,将一张对折的白色纸条压在了我摊开的掌心之下。
冰凉的手指甚至没有触碰到我的皮肤。
她没有任何停留,径直走向下一排。
心脏停跳了一拍。
我僵硬地、缓慢地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打印的宋体,冰冷得像一份机器生成的指令:
「最后一道题答错会死——不是比喻」
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彻底冰凉。荒谬感裹挟着巨大的恐惧攫紧了我。答错……会死?不是比喻?这是什么?一场恶劣的玩笑?一次迟来的、带着恨意的报复?她疯了?!
我猛地抬头看向她。
她正站在讲台旁,背对着大部分考生,面朝着我的方向整理已收回的部分答题卡。似乎察觉到我的注视,她抬起眼。
直直地看向我。
那不再是之前的全然漠然。那深井般的眼底的最深处,有什么东西在翻涌,极度焦急的、近乎绝望的警告!像冰封火山下终于压抑不住的熔岩!尽管只有一瞬,快得几乎让人以为是幻觉,但那确凿无误的惊惧狠狠刺穿了我!
紧接着,她的视线锐利地扫向我桌上的纸条方向,又急速回到我脸上一个极其微小的、几乎无法察觉的摇头动作。
快做!
我读懂了。
几乎是同时,“叮——”的一声悠长铃响撕裂空气。
“时间到!全体起立!停止答题!”另一名年长的监考老师高声宣布。
教室瞬间陷入一种喧闹的死寂——桌椅拖拉声、如释重负或懊恼的叹息声、纸张翻动声轰然响起。
而我僵在原地动弹不得。
因为就在林薇因 *** 响起而微微转身、裙摆轻扬的一刹那——
我清楚地看到,
在她纤细小腿应有的弧度之下,
连接的是一截冰冷、泛着金属哑光、结构精密绝非仿真的——
机械肢体。
 资讯网
资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