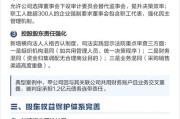梦到舅舅

昨夜,舅舅入梦来。
他仍是那副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头发乱蓬蓬地竖着,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我们站在老家的院子里,那棵枣树已经高过屋檐,青涩的果子在月光下泛着冷光。舅舅不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意味。我想问他这些年在那边过得可好,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然后梦就醒了,凌晨三点钟,窗外下着雨。
舅舅是五年前走的,肺癌。查出时已是晚期,从住院到离开不过三个月时间。母亲说,他走的那天格外平静,甚至嘴角还带着笑,像是终于解脱了。家里的老相册里有一张舅舅年轻时的照片:白衬衫,黑裤子,手里拿着一本《普希金诗选》,站在大学门口,眼睛里全是光。那是我从未见过的舅舅——我记忆中的他,总是在修理厂里满手油污,或是蹲在门口闷头抽烟。
舅舅曾经是个文艺青年。这是母亲告诉我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读的是中文系。那时候他写诗,投稿,参加诗会,还和一个女同学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毕业时,他却放弃了留校的机会,执意回到县城。“家里需要我”,这是他的理由。外公早逝,外婆身体不好,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正在读书。于是舅舅回来了,进了一家机械厂当技术员。
童年的记忆中,舅舅家是个神奇的地方。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堆满了书,从《红楼梦》到《时间简史》,从《战争与和平》到《机床维修手册》。墙上贴着他手抄的北岛的诗,工具箱里却放着各种型号的扳手和螺丝刀。他常常一边给我讲《小王子》,一边修理我弄坏的玩具飞机。那时我觉得舅舅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既能读懂那些厚厚的书,又能让所有坏掉的东西重新转动。
但生活从来不是童话。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舅舅下岗了。有段时间他天天骑着自行车出去找工作,回来时总是带着一身酒气。后来他东拼西凑买了些工具,在街角开了个修理铺。从此他的手上永远沾着洗不掉的油污,指甲缝里都是黑色的。那些书被装进纸箱塞到床底,诗稿也不知所踪。有一次我去找他,看见他正蹲在地上拆一台发动机,旁边放着半瓶白酒。那天他忽然抬头问我:“你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吗?”我没回答,他自顾自地说:“就是为了把这些破玩意儿修好。”
舅舅终身未娶。据说当年那个女同学后来出国了,给他写过信,他没有回。外婆临终前拉着他的手流泪,他说:“妈,我一个人挺好的。”可是我知道不好。每次过年团聚,他总是最早离开的那个;看到别人家的小孩,他会下意识地别过脸去;有次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独自在院子里看月亮,背影单薄得像一张纸。
现在想来,舅舅的一生都在修理东西——电器、车辆、邻居家的水管,还有这个家的一切。他修好了那么多东西,唯独没有修好自己的人生。那些未竟的诗篇、未曾说出口的爱、未能实现的理想,都化作深夜的叹息,消散在机油味弥漫的空气里。
梦醒后我再无睡意,起身翻出老照片。有一张是舅舅抱着五岁的我修玩具火车,他的手指粗糙但动作轻柔,眼神专注得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我突然明白,也许每个人都是修理工,用一生的时间修补残缺的生活、破损的梦想和漏雨的现实。而舅舅修得最用心的那件作品,是我——他教会我认字读书,告诉我要“像个人一样活着”,尽管他自己活得那么委屈。
天快亮时雨停了。我推开窗,看见东方的天空泛出鱼肚白。舅舅不会再回来了,但他修过的东西都还在正常运转:老家的挂钟依然准时敲响,邻居的摩托车还在路上奔跑,而我——他最得意的作品——正在学习如何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保持完整。
有些人来到世上,不是为了成就伟业,而是为了成为一座桥,让别人踏着走过深渊。舅舅就是这样的桥:他自己沉没了,却托起了整个家;他放弃了自己的诗和远方,却给了我追寻远方的可能。
梦中的枣树又结果了舅舅。今年的枣子格外甜,像是要把所有未说出口的话都酿进果肉里。我尝了一颗忽然泪流满面——原来最深的思念不是痛哭失声而是尝到甜时之一个想到却再也无法分享的人。
舅舅你看枣树又高了些而我想你了。
 资讯网
资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