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味的消逝:太原苹果与现代性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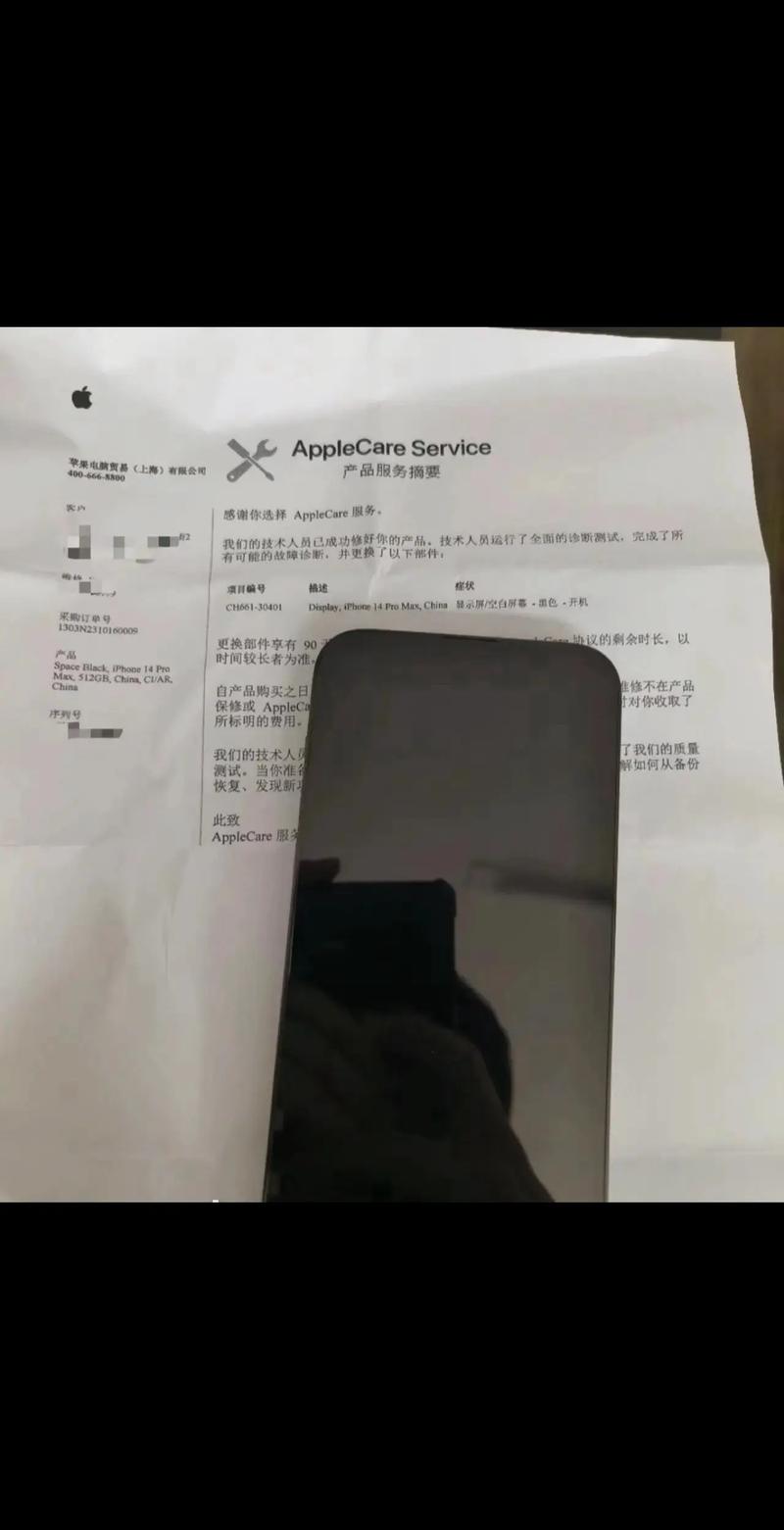
太原城郊的果园里,最后一棵老苹果树被连根拔起时,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叹息。这声音被挖掘机的轰鸣所淹没,却在我的记忆深处回荡不去。那棵树上结的苹果,酸中带甜,果肉微沙,咬下去有种独特的颗粒感——那是属于太原的味道,是我童年味觉版图上最鲜明的坐标。
小时候,外祖父总是带着我去果园。那些苹果树不高,枝干虬结,树皮粗糙如老人的手。“这品种叫‘祝光’,太原水土养出来的。”他摘下一个青红相间的果子,在衣袖上擦擦便递给我。那味道初始清酸,继而回甘,最后留在舌尖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芬芳。外祖父说,这是黄土高原的味道,是汾河水系的味道,是太原人世代耕读传家的味道。
那时的苹果各有其味:“红玉”酸得让人皱眉,“国光”脆甜多汁,“金星”香气扑鼻。每个品种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和忠实的食客。秋天来临,家家户户的地窖里储藏着不同时期的苹果,整个冬天,太原人的味觉都不会寂寞。
变化来得悄无声息。先是超市里的苹果变得整齐划一,那些熟悉的品种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完美无瑕的“红富士”,大小相同,颜色均匀,甜得单调而直接。老果园被房地产项目吞噬,新品种果树在农业示范区里整齐排列,像接受检阅的士兵。
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位守园人时,他正蹲在地头抽烟。“全都得砍掉,”他吐着烟圈说,“这些老树种,产量低,外观不匀,卖不上价。”他的身后是几棵仅存的老树,枝头零星挂着几个果子,在秋风中微微晃动,仿佛知道自己大限将至。
现代农业科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产和标准化。通过基因筛选、化肥催熟和保鲜技术,我们终于实现了苹果的全年供应和外观统一。可是当我们咬下那些完美的苹果时,却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所有的苹果都一个味道,甜得单调,缺乏个性,没有记忆中的那种复杂层次。
这种甜味的 homogenization(同质化)不仅是味觉的单一化,更是地方性知识消逝的隐喻。太原苹果的特殊风味来自于特定的土壤成分、气候条件和栽培技艺,是人与自然长期互动的结果。而当这种风味消失时,随之消失的是一整套关于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智慧。
更令人忧思的是,我们正在以对待苹果的方式对待自己。教育体系生产着标准化的人才,都市景观变得越来越相似,甚至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在大数据算法的塑造下趋于一致。我们获得了效率和经济性,却失去了多样性和地方性——那些使生活值得留恋的微妙差别。
那个下午,我从守园人那里买下了最后一批老品种苹果。带回城里分给朋友时,大多数人只是礼貌地表示感谢。“有点酸呢,”有人委婉地说,“不如超市买的甜。”只有一位老人尝了一口后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这是‘祝光’吧?多少年没吃到这个味道了。”
我想起外祖父生前说过的话:“一棵树要知道自己长在哪里,一个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当我们为了追求统一的“甜”而消灭所有其他味道时,我们是否也在抹去自己与土地的最后联系?
或许真正的进步不是用一种味道取代所有味道,而是让不同的味道都有存在的空间。在太原的老果园消失的地方,高楼拔地而起,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而我则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寻找着那些即将消失的味道——不仅是为了怀念过去,更是为了证明:在这个日益扁平化的世界里,差异本身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每一口有故事的苹果都在提醒我们:甜味不应只有一种标准,美好生活也不应只有一种模样。在标准化与多样性之间,在全球化与在地性之间,我们需要找到某种平衡——否则当最后一种老苹果消失时,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与世界相处的一种方式。
 资讯网
资讯网



